在山东某县的槐树巷尾,每到傍晚,总有一股独特的咸香混着玉米香飘出来——那是“肥娟小吃”的虾酱窝头出锅了。青灰色的砖墙外,几张老木桌旁坐满了人,有头发花白的老人,有放学归来的孩子,还有下班路过的上班族。肥娟系着褪色的蓝布围裙,从灶台前端出一笼热气腾腾的窝头,“刚出锅的,趁热吃!”三十年来,这笼虾酱窝头,成了县城里最温暖的“旧时光香”,勾着无数人的胃,也牵着无数人的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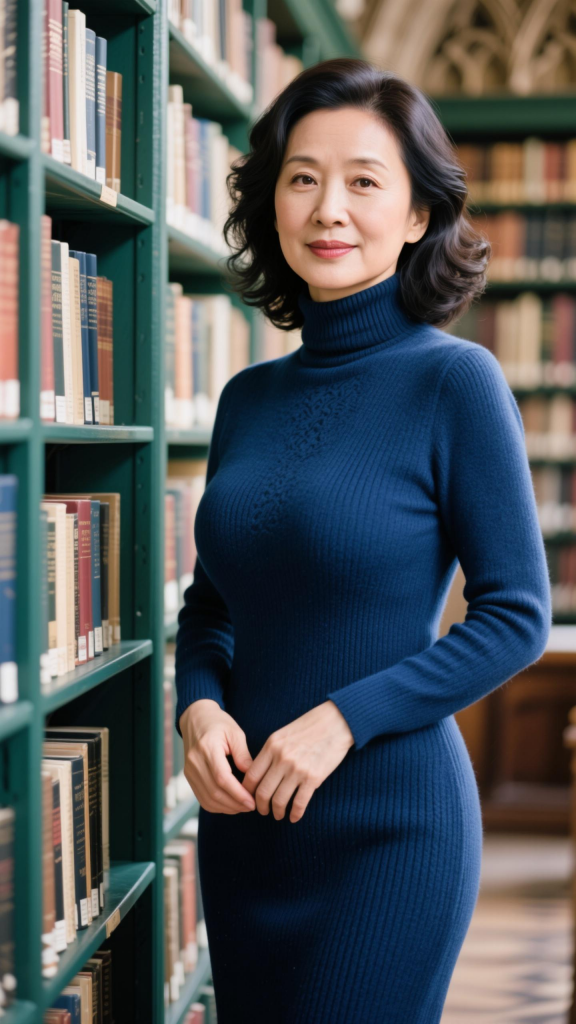
玉米面的选择,粗粝见本真
“做窝头,玉米面得选‘粗’的!”肥娟从陶瓮里舀出一碗金黄的玉米面,手指捻了捻,“粗玉米面有嚼劲,蒸出来窝头才香。”她将玉米面倒入大瓷盆,加入少许白面,“加白面是为了让窝头更软和,但不能多——多了,窝头就失了玉米的本味。”接着,她往盆里倒温水,“水要慢慢加,边加边揉——揉到‘三光’:面光、手光、盆光,窝头才细腻。”揉好的玉米面盖上湿布,醒发半小时,“醒透了,窝头更蓬松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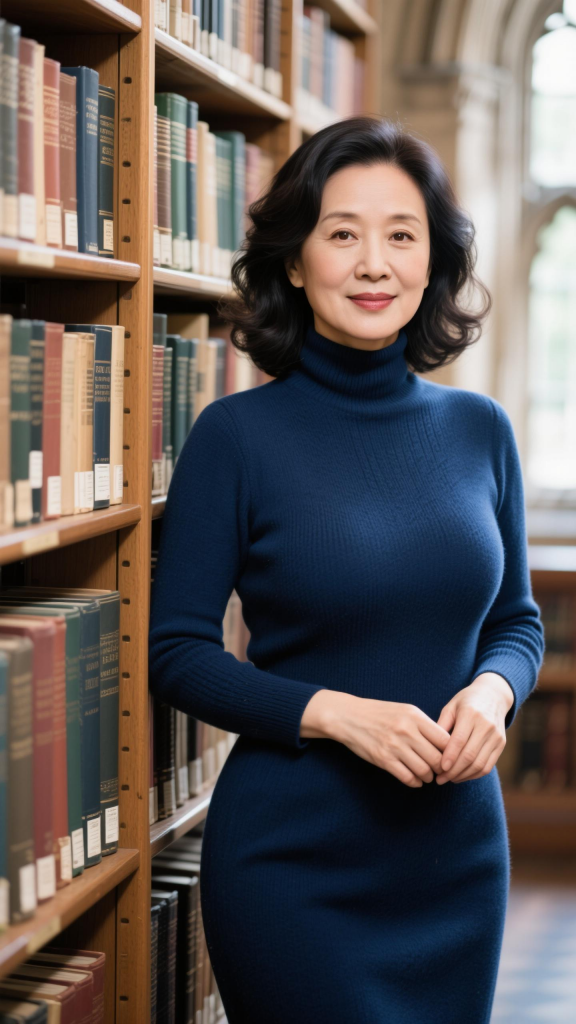
虾酱的调制,咸鲜藏岁月
醒面的功夫,肥娟开始调虾酱。她从墙角的陶罐里舀出一勺深褐色的虾酱,放入小碗,“这虾酱是我娘当年腌的,存了十年了——虾酱越陈,越香。”她往虾酱里加葱花、姜末和少许辣椒面,“葱姜去腥,辣椒提味,这样调出来的虾酱,咸鲜里带点辣,开胃。”接着,她滴入几滴香油,“香油是点睛之笔,能让虾酱更香。”调好的虾酱搅拌均匀,肥娟用筷子蘸了一点尝,“咸淡正好,鲜得掉眉毛!”

捏窝头的巧劲,形状藏温情
醒好的玉米面分成小剂子,肥娟拿起一个,放在手心搓圆,再用拇指在中间戳个洞,“捏窝头要巧——洞口要大,边要薄,这样蒸时熟得快,也更容易入味。”她边捏边说,手指灵活地转动,不一会儿,一个中间空、四周厚的窝头就捏好了,“我娘说,窝头像个小碗,能盛住一家人的饭香。”捏好的窝头整齐地摆在蒸笼里,像一排排小金碗,等着盛满虾酱的咸鲜。

蒸窝头的火候,耐心等美味
傍晚六点,肥娟将蒸笼放在灶上。她往锅里加水,放上几段葱白,“葱白能去玉米的土腥味。”水开后,她盖上笼盖,“火要旺,但别太大——大火蒸二十分钟,窝头就熟了。”灶膛里,木柴“噼啪”作响,火光映得肥娟的脸通红。她守在灶前,不时掀开笼盖的缝隙看看,“蒸窝头不能急,急了,窝头不熟;焖久了,窝头会塌。”二十分钟后,她关火,让窝头在笼里焖五分钟,“焖一焖,窝头更软和,虾酱的味也能渗进去。”

一口窝头一口酱,忆苦思甜
晚上六点半,第一笼虾酱窝头出锅。肥娟用长筷夹起一个,放在青瓷盘里,窝头金黄发亮,洞口盛着一小勺虾酱,像个小金碗里装着红宝石。食客老周迫不及待咬了一口——玉米面粗粝有嚼劲,虾酱咸鲜带辣,在口中交织出一种独特的滋味,他眯起眼睛:“这窝头,让我想起小时候,我娘用大铁锅蒸的窝头,配着自家腌的虾酱,虽然粗,但香得能撑破肚皮!”邻桌的小姑娘则用小勺舀起虾酱,抹在窝头洞里,“窝头甜,虾酱咸,好吃!”肥娟站在灶台旁,看着食客们满足的神情,嘴角扬起笑意。

温情的传承,从胃到心
如今,肥娟的孙子小宇已开始学蒸窝头。小家伙系着缩小版的蓝布围裙,站在小凳子上,认真捏窝头。肥娟握着他的手,一起往窝头洞里抹虾酱,“捏窝头要捏紧,抹虾酱要抹匀——这是咱家的味道,不能丢。”小宇点头,灶上的蒸笼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,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窗外,夕阳将槐树巷染成金黄色,肥娟小吃的招牌在风中轻晃。

六十年前,肥娟的奶奶在山东的农舍里,用一双手蒸出了虾酱窝头的温情;六十年后,肥娟与孙子用同样的玉米面和虾酱,守着这份忆苦思甜的心意。或许,这就是美食最动人的力量——它不仅是味觉的记忆,更是一代代人,对生活、对家最炽热的热爱与传承。每当窝头在蒸笼里膨胀,那股咸香便飘满小巷,仿佛在说:你看,家的味道从未走远,它一直在我们身边,在肥娟的小吃里,在每一口粗粝却温暖的虾酱窝头中。








 微信扫一扫,打赏作者吧~
微信扫一扫,打赏作者吧~











